 产品展示
产品展示 产品展示
产品展示时间: 2025-04-24 21:33:24 | 作者: 产品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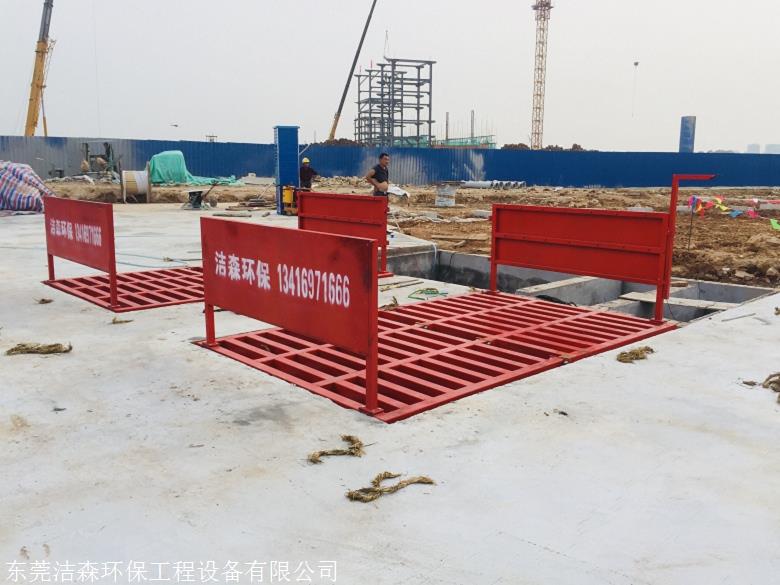
与资本主义动力逻辑类似,所有社会的动力逻辑都是“控制人“对社会基本动力进行变造以实现其特定功能的存在物。我们只要将 “资本控制”替换为相应社会的控制元素就可得到其本身的动力逻辑,社会的性质也是由此确立的。
如我们以“皇权控制”,“专权控制”,“奴隶主控制”,“封建主控制”,“宗教主控制”进行代换,社会就变成了历史上现出过的相应制度的模样。欧洲中世纪是“宗教主控制”下的社会,用“宗教主控制”来替换“资本控制”,这一社会的动力逻辑也就跃然纸上了。
但社会主义与历史上的其它社会制度均不相同。这是唯一一个以“主义”作为主导控制元素的社会,这是与其它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其它社会制度虽然也有为其声称的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但除了社会主义其它社会的“主义”都不能成为主导社会运行的控制元素,不过是特定群体用以图利的手段。包括在宗教统治社会中,介入到世俗事物的教义一般成为胁迫他人遵从教主利益的手段。
社会以“主义”控制同以“利益”控制存在巨大不同。人一直声称坚守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不忘初心,且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因而成为了一个以“主义”塑身的群体,再既而以“主义”塑造社会。人的目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吗?这是肯定的!要求我们在专门篇章中讨论。有人称人的信仰行为如同宗教,这定然是错误的,同样是需要我们另行厘清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政策、制度、法律都是围绕“主义”展开的,体现服务于“主义”的性质。并非说不存在假借“主义”者进行利益贪图,而是:
其一无人敢公然背弃“主义”另行主张自己或群体的特殊利益,除非有办法让绝大多数人放弃其所认同的“主义”。
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变并不是无产者们或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者以“修车”为手段,诱使人们用“民主”之类的“功能件”掉了决定社会性质的“主义”这样的“根本件”。无产者的“主义”的正当性资本主义者从来未能真正否定过,但利用当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修车”为手段最终把“修车”变成了“换车”。
其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当社会出现有冲突性的问题时,“主义”就会成为人类论证自身主张正确的根据,并成为凝聚社会共识,获得广泛支持的关键。“主义”由此成为社会的定海神针,纠偏利器。这对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以下简称无产者)极具意义。
正因为“主义”不能被人公然背弃,无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出现怎样的偏差最终总要回归到“主义”的要求上来,“主义”与生命具有的基因一致,成为无产者队伍、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基因。
“主义”实际是在无产者反抗剥削压迫者的斗争中及在马恩指导下所形成的人民大众的共识。需要明了这个共识并不是马恩创造的,且同样不是无产者的领导团队即无产阶级政党或称组织总结及创造出来的,完全是无产者队伍共同认定形成的。恩格斯称: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原因也就在于此。
马恩对“主义”的真正贡献是为无产者们设计了一个可在社会现实中使“主义”得以实现的路径,或说相应的路径参考。苏联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参考了这个路径,且结合实际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参考了马恩的路径设计,并大力参照了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行了更大幅度的调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这样的产物;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更是这样的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完全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成为真正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下来的社会主义大国,成效使人惊艳。
在此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和马恩思想做一个区分。马克思主义实际属于在马恩指导下,对无产者的主张进行概括与总结从而形成的无产者的共识。“主义”的根本就是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让人类能够解放自己,使人人都能得到自由。马恩思想则是马恩对“主义”实现路径进行的求索,以理论家的视角为无产者论证了“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前者无产者及组织领导队伍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背离的,这是共同的主张;对于后者需要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通过践行来落实,并要适应实际来调整、完善,还要根据发展变化展开新的探索和创新。
对于无产者“主义”是全体成员立身社会的护身符,由无产者建立的政党则是为无产者承载“主义”在社会中践行的决定性力量。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来承载“主义”及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无产者将被各种势力所分化,是无力将“主义”付诸社会实践的。
当今一众高知者持续鼓吹只有仿照西式民主人民才能取得当家作主的权力。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无产阶级的“主义”,去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最终让无产者就此丧失当家作主权力的重要手段。表面上这是在让所有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实际上这是在社会的不当环节为大众设置的一个民主陷阱。
利用无产者们在这一环节为有关问题产生纷争的办法,转移无产者关注的问题重心。特别是利用定期民主的方式,在思想主张与利益的纠葛中让人们每次都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主义”由此为之淹没。无产者会忽视原来共同达成的“主义”,关注点被集中在对现有问题的纠纷上,并将自己及有共同主张者能否在每次纷争中“取胜”作为一切的重心。无产者队伍定然由此发生离散。
同样,通过定期民主选举方式,无产者群体将因为问题纷争而各自去推举让自身更合意的领导团队,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力量也必然由此分裂,这将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权力利益会变身为组织领导权力争夺的重心,“主义”变成争夺人群的招牌物。无产者亦将失去对组织领导群体的信任,组织领导群体同样会丧失对无产者队伍再行统一领导的可能。无产者们以统一力量为自身争取社会利益的可能性,及对社会按照自身“主义”实现治理的可能性也将就此丧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着手模仿西式民主举行立宪会议选举。最终结果是在农民中更具影响力的社会革命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要说选举中的工人无产者与贫困的农民都当是反对剥削压迫的支持者,都应支持为此组织起革命并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布尔什维克政党。选举前的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自身必然会得到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结果相反。这是仿照西式民主导致问题的生动例证。这样的民主只会让无产者的“主义”在无形中被灭失,面对被撕裂的社会大众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自然丧失掉统一进行组织领导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的社会领导权只会由此被葬送。
无产者们需特别明了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人类历史上对他人最具剥削压迫能力的群体(这样的社会精英),无论在认知判断学习力上,组织领导和资源控制力上,突破固有思维逻辑的创造力上、 破除心理阻碍的调适力上,等等方面,均远超于绝对多数的被剥削压迫者群体。无论这些人是来自于社会的上层还是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均具有这样的“超能力”。
相应而言被剥削压迫者必须依靠具有同样能力甚至超过上述能力的先进分子,包括先进的知识分子及信仰坚定、勇于牺牲、组织领导力强的群体骨干——也就是自己的政党,将人们组织起来。只有通过他们强有力的领导,自身才能此来与上述的“超能力”者们抗衡及至压制住他们的相关行为。不如此,无产者们是无力与这些“社会精英”剥削压迫行为相抗的,只会为之分化、控制,受其支配、压迫。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庞大的被压迫者群体长期都处于为人分化、控制,和被人支配、受人剥削的状态,不建立主义,不经有效组织是不可能使之发生改变的。
因此,无产者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组织领导团队即无产阶级政党,更不能为西式民主所蛊惑,照搬其样式,让自己的“主义”为之,及让自身的队伍为之离散。马恩、列宁、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有过相应的实践批判。
民主在社会治理行为中只是一个功能物。应该要依据社会实际,本身的制度体系、相应的方面和运行层次的情况,以及相关目标和治理要求选择相应的民主样式,并安放在所适宜的环节和时间节点上来发挥其功用。并非是在社会全部系统中和全部运行环节上都进行安放,或仿照资本主义的制度样式进行安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有不一样的运行系统,遵循的是不同社会运行规律,在治理要求及目标上有着本质差异,一定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进展民主的构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要求。
相应而言当下无产者拥有的“主义”与“党的领导”早已是自身“全过程民主”的既定物。是“全过程民主”先期已取得的一个结果,且这个民主的过程至今仍在延续之中。
达成“主义”、“党的领导”共识的民主开启于无产阶级开始觉醒并组织起来开始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时期。这个民主的开端极其惨烈,是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一是建立“主义”阶段。也就是无产者达成民主共识的阶段,此阶段就形成“主义”而言已经完成。
二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此阶段也已进行了一个过程,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被建立了起来,但有相当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被诱入资本主义的民主陷阱,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
三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阶段当极其漫长。中国将自身当前的社会主义阶段定义为初级阶段,还应存在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初级阶段必然是极度不成熟的,不断会有问题聚集,不断要去克服问题,要极力防范各种风险,是砥砺前行的阶段。
四是“主义”完全实现阶段,也就是可让人类得到彻底解放的阶段。无疑这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为基础,没有充分发达的社会条件人类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
资产阶级一直在向世人宣扬所谓权力要有合法性来源,所谓主权在民等。那么无产者通过个人的民主方式确立起来的“主义”及将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为自身的领导团队,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是通过无产阶级民主取得的结果。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后,无产者不需要再行用民主方式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义”和组织领导团队,否则等同于让人们质疑原来通过革命所确立的“主义”,质疑革命先烈所做出的牺牲和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是质疑自己主张的正当性。
这正是资产阶级让无产者的“主义”及已组织起来的队伍变得不定性且要反复定性的办法,无产者“主义”及领导者队伍必然因此丧失稳定性,及持续指导、领导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在资本主义民主下无产者的“主义”及领导者队伍会在不同思想、不同主张的反复冲击下,最终变成破碎、不能再有所为的存在。
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构建自己的样式,一定要符合自身社会性质与制度要求,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终归来说要从所要实现的功能需要出发来设定社会主义民主。结合于社会治理目标、要求,适应于社会治理的相应方面和层面,针对运行环节及时点处理问题的需要进行设计和安放。资本主义民主样式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适物。在红军队伍中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就是对无产阶级民主样式的实际示范。
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不受制约。实际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为官僚权力所破坏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在为之所破坏。反腐真正要解决的就是官僚权力的问题。而要从根本上去除官僚利益,在相关环节上建立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民主或是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如何施行需慎重抉择。特别是不能将西式民主照搬过来,这等于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无产者对此要要有清醒认知,不能为了纠正问题而颠覆掉自身的制度根本。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者们想要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只会是黄粱一梦。资本只会在自我获利中因其不得已的原因而给他人以捎带的好处。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自己都要承认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这个“不得已”的产物之一。资本家在整个世界布设他们的资产,只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给他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当今世界社会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就是资本制度所导致的。
当然社会主义在其必要的发展阶段,在欠缺完善的情况下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是必要的。特别是当无产者还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合格主人,队伍中还有众多与剥削者诉求相一致的“特洛伊木马”持续破坏着无产者队伍努力成果的情况下。在自身欠缺处理问题的可用方案时,借用一下他人的可行方案实际是一种最佳策略选择。
由此来看社会主义的动力控制逻辑,无疑这就是一个由“主义”+“政党”所构成的一个控制核心。所要达成的控制结果就是要保证“主义”的最终实现。在社会的全部运行阶段上都要防止与“主义”相脱离,这是一个以“主义”进行持正的控制,不妨将社会主义的控制元素命名为“持正控制”。社会主义的动力逻辑式如下:
“无产者利益”不能被理解为无产者要谋取特殊利益。正如马恩所指出的,无产者只有解决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而利用“持正控制”对利益进行调正时更应强调:要首先保证为社会做出贡献但缺乏为自身争取正当利益能力的底层群体的利益。